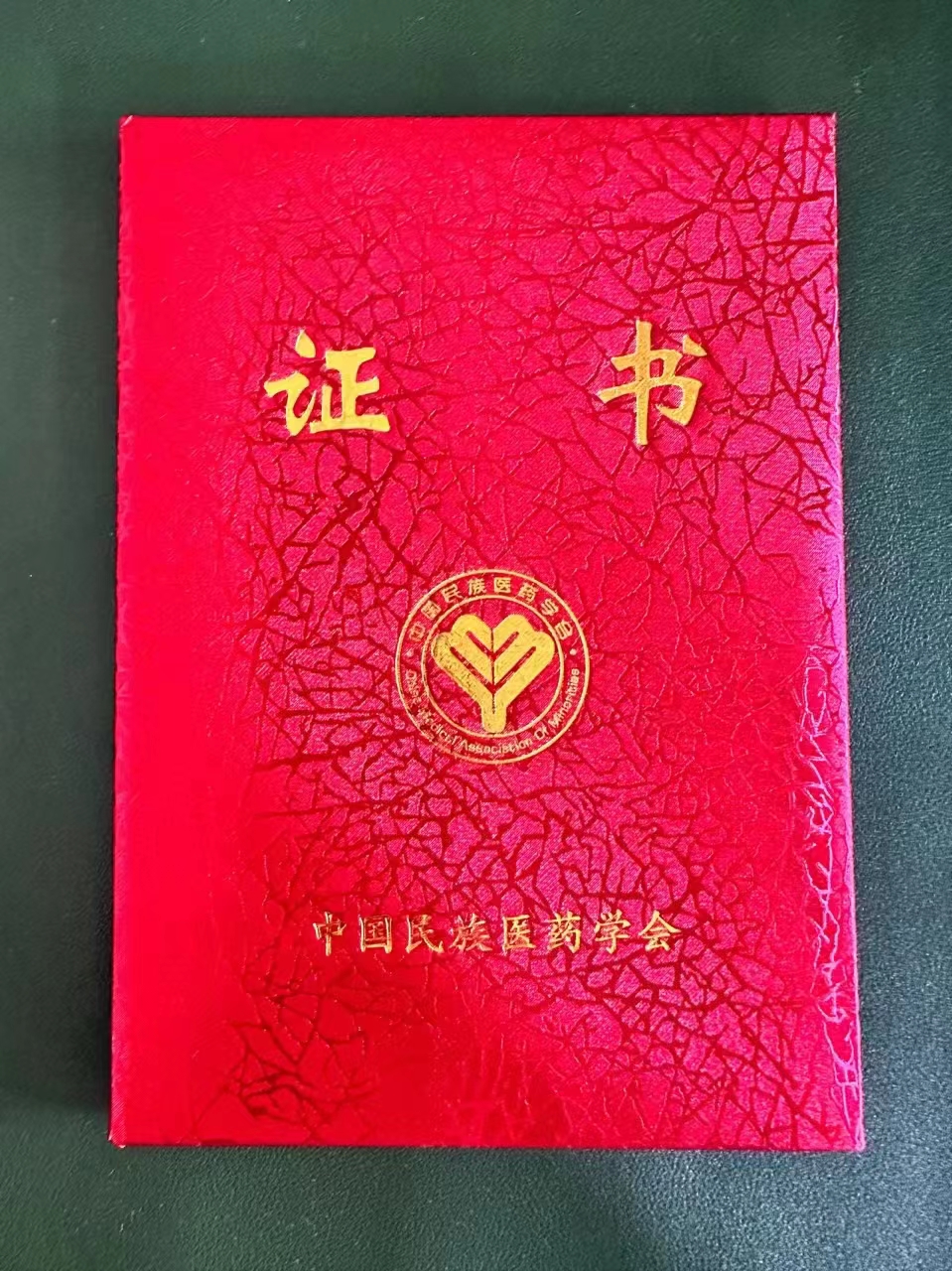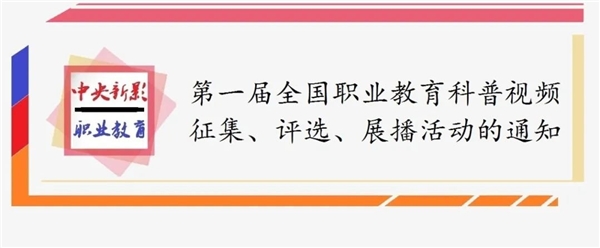吴家琳在的《Life After Death》这件作品中所表达的并非对死亡的视觉再现,也不是关于哀悼或纪念的图像化装置。《Life After Death》是一件关于“存在残余”的艺术提问——在物质性终止之后,什么依旧存续?在被归类为“结束”的之后,艺术是否能重新唤起一种持续的存在状态?
这件作品拒绝叙述性,也拒绝象征性的视觉语言。正因如此,它所生成的不是感官的冲击,而是认知系统中的震荡与悬疑。它并不制造“死亡”的形象,而是转向死亡之后,那段被语言无法命名的时空褶皱。观者所面对的一种没有明确语境、不再受线性时间控制的中介状态。
在这件作品中,吴家琳所使用的媒材不强调物理张力,而是着力于生成一种非物质的场域——这是一种“感知中的剩余”,它不具象,不表态,却持续对观者的身体发出召唤。它不直接构成经验的主体,而是作用于经验的缝隙,让我们注意到那些被忽略、被视为“不足以成形”的感受。正是在这种几乎隐性的媒介策略中,她构建起了“死亡”之后感知系统的微观建构。

从艺术语言上说,《Life After Death》是一种“现象学式”的装置思维。它既非剧场性,也不属于纪念性美学,而是一种更加内倾的、以身体感知为主轴的艺术实验。在吴家琳看来,死亡不该被具象化,因为任何具象的死亡描绘都可能转化为叙述暴力。而真正需要被处理的,是死亡之后的无形残留——那种无法言说、无法辨识、但却持续作用于我们知觉系统中的“存有的回声”。

也正因如此,观者在面对这件作品时,被迫放弃解释的冲动,而转向一种更基础的、近似于冥想状态的观看方式。这种观看不是在寻找意义,而是在聆听:在试图聆听那种极低频、濒临沉默的震动。这是一种“在场性”的转译,它不靠图像也不依赖文本,而是靠一种极端稀薄的、几乎被遗忘的身体记忆形式去构成。

吴家琳在《Life After Death》中所讲述的不是谁的死亡,而是“死亡如何被感知”。而更进一步地,它提出的不是“死后是否存在”的问题,而是“死后感知如何延续”的命题。这一转向,是艺术介入生命哲学的独特路径。在当代艺术语境中,面对死亡主题的创作往往陷于两极:要么是极端的纪实化叙事,要么是抽象的美学装饰。但吴家琳拒绝这两种路径。她选择一种无声的、去叙述的、几近消散的形式策略,从而实现一种感知转译的美学抵抗。她以“缺席”为语言,以“未完成”为结构,以“失语”为诗性。
《Life After Death》是一段尚未结束的频率,一个不断延迟的低语。它将我们引入一种对“存有残响”的重新体认之中——在那里,死亡不再是时间的断点,而是感知的暗涌,是存在在不可见维度上的持续回声。
责任编辑:冯至